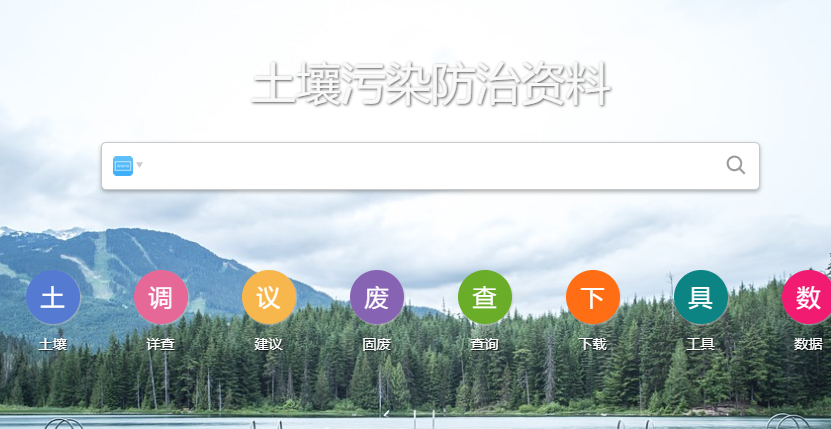不同国家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比较与启示
摘要: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影响农产品质量、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经过十几年的修订,我国于2018年发布了《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土壤污染防治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当前有关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相关的综述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17个国家或地区的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从标准体系、保护目标、制定方法、覆盖指标、分析方法、标准数值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用地风险管控标准污染指标较少、均为总量指标,且制定过程缺乏标准化的推导方法.因此,我国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仍需要持续地补充、修订和完善,建议后续加强农用地土壤环境基准和背景值等基础研究,建立科学、规范基准和标准制定方法,逐渐完善风险管控标准指标数量、形态和有效性指标,同时鼓励建立区域和地方配套农用地标准,为我国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的优化和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 农用地 土壤风险管控标准 农产品质量安全 生态安全 生物有效性
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关系人民群众健康, 关系美丽中国建设, 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因土壤污染引发的污染危害事件逐年增多, 尤其是农用地土壤污染, 严重影响着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1, 2].根据2014年《全国污染土壤环境调查公报》报道, 我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 而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 工矿业和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3].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不仅影响农产品质量和农作物生长, 同时影响土壤生态安全, 包括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地下水、地表水和饮用水的安全等.因此,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和“水缸子”安全, 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子孙后代生存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4].
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针对农用地, “土十条”提出明确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出发点,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和风险管控; 要求到2020年, 农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确保到2020年,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 到2030年,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提出对农用地实施分类管理, 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 2017年底前发布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为落实“土十条”要求, 切实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于2018年正式实施[5].新修订的《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指出, 风险管控标准“为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公众健康, 推进生态环境风险筛查与分类管理, 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控制生态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和因素”而制定.因此, 与水、空气质量达标目标不同, 新修订的土壤风险管控标准提出了筛选值和管制值两条线, 适应土壤风险管控的思路, 进行风险筛查和分类, 对有效管控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和加强土壤环境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土壤环境标准需要持续地补充、修订和完善.与我国相似, 为配合各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 部分国家和地区针对农用地制定了相关的土壤环境标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用地土壤环境保护目标、污染物指标、制定方法和应用场景等各不相同.德国于1998年颁布了《联邦土壤保护法》, 1999年配套《联邦土壤保护和污染地块条例》, 该条例规定了农用地预防值、触发值和行动值这3类土壤污染限值[6].荷兰于2009年提出可持续土壤治理概念, 以背景值作为农用地和自然用地的土壤环境标准[7].日本直接以稻米镉标准作为农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8].此外, 一些国家为保护农用地使用人制定相应的土壤环境标准, 如英国租赁用地的土壤指导值[9]和加拿大农用地的保护健康和生态的土壤质量指导值[10].与上述国家相比,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当前与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相关的综述研究相对较少.因此,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国家或地区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的标准体系、保护目标、制定方法和应用情景等方面进行研究, 归纳得出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 提出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基准研究和标准修订的建议, 以期为我国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的优化和完善提供参考.
1 不同国家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比较1.1 标准体系
由于各国在地理环境(影响土壤污染物暴露的区域性因素, 如降雨、降雪、土壤类型、地下水深度和地表水等)、生物环境(影响人群或生态受体敏感性因素, 如体重、寿命和敏感物种等)、社会文化(影响土壤污染物暴露的因素, 如社会行为和土地利用方式等)、管理政策(土壤污染管理需求、法律和法规等)和科学基础(土壤防治科学的理论基础)等方面差异, 各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各不相同, 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在定义、推导和使用等方面也不尽相同.最直接反映这些差异的是标准名称的不同, 包括筛选值、管制值、触发值、清洁标准、限制、指导值和环境质量标准等.
尽管各国或地区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存在差异, 但根据其标准功能和对应的相应风险等级将各国标准大致划分为指示可忽略风险的标准值、中等风险的标准值和不可接受风险的标准值.如表 1所示, 可忽略风险标准是土壤环境保护的长期目标, 低于该值表明无风险, 通常该值略高于土壤背景值, 少数国家也直接以背景值指示可忽略风险, 然而我国暂未制定农用地的可忽略风险标准或背景值; 中等风险标准与该土地利用方式下假设的保守情景相关, 一般低于该值表明风险可接受, 高于该值应开展进一步调查甚至风险评估工作, 根据调查结果选择相应的安全利用措施, 如我国土壤风险筛选值和德国土壤筛选值等; 不可接受风险标准旨在防治对土壤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般高于该值应采取相应的修复治理和风险管控措施, 如我国土壤风险管控值、奥地利干预值和波兰土壤质量指导值等.
不同国家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的法律执行力度也有所不同.部分国家土壤标准是强制性的, 只有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才可采用其他限值, 如根据风险评估计算的特定土壤筛选值; 部分国家土壤标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可作为土壤调查中的推荐值, 也可直接作为修复目标.
1.2 保护目标和推导方法
如表 2所示, 国内外制定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时主要从保护农产品安全、人体健康、生态安全和地下水安全等4个方面获得相应临界含量或阈值.其中, 保护农产品安全的土壤标准通常基于土壤-作物迁移模型和食品、饲料等卫生标准来制定, 以农产品中污染物浓度达到相应标准为保护目标.多元回归模型和物种敏感性分布法(SSD法)是普遍采用的土壤-作物迁移模型.保护农用地使用人人体健康的土壤标准采用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学制定[20].各国根据合理保守原则构建本土化的特定暴露场景(概念模型), 主要暴露途径包括室内粉尘吸入、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食用自产作物(蔬菜、水果)和食用附着在自产作物上的土壤和饮用地下水等.少数国家考虑食用鱼类、肉类和乳制品等其他暴露途径, 或是将其纳入背景暴露范畴.
保护生态系统安全的土壤环境标准包括保护农作物生长和保护土壤生态环境.其中, 保护农作物生长主要考虑土壤污染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以保持土壤良好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通常采用生态环境效应法[21]; 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采用生态风险评估方法学[22], 评估污染物对陆生生态系统的直接接触毒性或经过生物累积的二次毒性, 推导方法包括SSD法、评估因子法(AF法)和平衡分配法等[22].保护地下水安全的土壤环境标准是基于土-水迁移模型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来制定.本次调研仅比利时瓦隆地区和加拿大计算了保护地下水的土壤临界值.我国已废除GB 15618-1995标准二级标准中原先考虑了土壤-水环境, 以不引起水体次生污染为原则, 基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推导[23].
当前, 我国GB 15818-2018标准以保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主, 同时兼顾保护农作物生长和生态环境的需要.与国外农用地标准相比, 我国农用地更加关注保护食用农产品质量, 以食用农产品的消费者为主要保护目标.而国外农用地土壤标准更加关注农用地土地使用人的人体健康.实际上, 国外在制定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环境标准时已经把摄食自产的农产品作为间接暴露途径予以考虑, 而普通消费者接触农产品的暴露途径往往归属于背景暴露.部分国家如加拿大在建立农用地土壤质量指导值时, 同时要求计算的指导值应保证自产作物中污染浓度应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1.3 污染物指标、测试方法和标准值
各国在制定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时, 选择保护对象、制定方法、所用模型和参数各不相同.因此, 各国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在污染物指标选择、形态特征和浓度数值上存在较大差异, 部分污染物标准值存在数量级的差异[24].
如表 3所示, 各国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涉及29个重金属及其他无机物指标.按国家指标数量排名, 土壤标准中重金属及其他无机物指标数排名前六的国家(地区)为加拿大、捷克、中国香港、荷兰、奥地利和波兰, 我国土壤风险管控标准8种重金属指标数相对较少; 按污染物指标数量排名, 超过10个国家制定标准的无机污染物指标分别为Cd、As、Pb、Hg、Ni、Zn、Cu和Cr, 上述8个指标我国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基本项目一致.
各国重金属标准主要采用总量指标, 少数国家制定提取态指标[24].检测方法我国主要采用盐酸-硝酸-氢氟酸-高氯酸的“四酸消解法”, 国外主要采用王水法(提取除晶格外的所有重金属), 因晶格内的重金属难以释放到环境中, 因此更能客观反映重金属的土壤污染风险.提取态指标国外主要采用硝酸铵提取法.
如表 4所示, 各国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涉及9类有机污染物指标, 包括烃类、芳香烃类、多环芳烃类、卤代烃、二英、多氯联苯、农药类、石油烃类和其他有机污染物类.按国家指标数量排名, 土壤标准中有机污染物指标数排名前五的国家(地区)为荷兰(8类、82种)、加拿大(8类、63种)、比利时布鲁塞尔(7类、46种)、比利时佛兰德(6类、45种)和中国香港(8类、37种), 我国土壤风险管控标准有机物指标数相对较少, 仅涉及苯并[a]芘、六六六和DDT; 按污染物指标数量排名, 超过10个国家制定标准的有机污染物主要为多环芳烃、芳香烃、卤代烃和多氯联苯类; 具体到污染物, 苯并[a]芘、苯、乙苯、甲苯、二甲苯、多氯联苯、萘、荧蒽、苯并[a]蒽和等10种有机物制定标准最多.
不同国家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值比较见图 1.与国外相比, 我国风险管控标准镉元素标准值较严格, 镉筛选值0.3~0.8 mg ·kg-1, 均低于50%分位值(1.50 mg ·kg-1), 管制值1.5~4 mg ·kg-1, 介于50%和75%分位值(4.00 mg ·kg-1)之间; 砷、铅和铬元素标准值相对较松, 其中砷筛选值20~40 mg ·kg-1, 介于25(20.00 mg ·kg-1)和75%分位值(45.00 mg ·kg-1), 管制值100~200 mg ·kg-1, 远大于75%分位值, 铬筛选值150~350 mg ·kg-1, 介于50%(130mg ·kg-1)和95%分位值(940.00 mg ·kg-1), 管制值800~1 300 mg ·kg-1, 远大于75%分位值(192.50 mg ·kg-1), 铅筛选值70~240 mg ·kg-1, 介于5%(39.25mg ·kg-1)和75%分位值(277.50 mg ·kg-1), 管制值400~1 000 mg ·kg-1, 大于75%分位值; 我国汞筛选值0.5~3.4 mg ·kg-1, 管制值2~6 mg ·kg-1, 基本位于25%(0.6 mg ·kg-1)和75%(5 mg ·kg-1)之间; 我国果园铜筛选值相对较严(150~200 mg ·kg-1), 大于75%分位值(150 mg ·kg-1), 其他农用地筛选值50~100 mg ·kg-1, 小于50%分位值(100 mg ·kg-1); 我国土壤镍筛选值60~190 mg ·kg-1, 其中2个标准值低于50%分位值(70 mg ·kg-1), 2个标准值大于75分位值(100 mg ·kg-1); 我国土壤锌筛选值相对较严(200~250 mg ·kg-1), 位于50%(200 mg ·kg-1)和75%分位值(300 mg ·kg-1)之间.此外, 我国农用地有机污染物标准相对适中, 苯并[a]芘、DDT和六六六标准值均处在50%分位值左右.
1.4 生物有效性
土壤作为异质性强的环境载体, 区域差异极大.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土壤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不确定性, 不同的土壤理化性质、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式和受体类型等都会影响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25, 26].有研究指出土壤污染物的风险主要由有效态部分的污染物浓度造成.目前, 各国土壤标准值主要是以一定标准土壤条件推导, 以全国统一的土壤污染物标准值有利于提高土壤污染评价的可比性和操作性, 但在实际应用中, 由于不同区域土壤理化性质差异极大, 对土壤中污染物生物有效性影响显著, 使得单一标准值在实际土壤污染调查和评估中往往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27].
如表 5所示, 部分国家在制定土壤环境标准时, 充分考虑土壤理化性质、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式和受体类型等因素对土壤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影响, 具体可分为3种方式: ①根据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类型对土壤标准值进行分类表述, 如我国根据土壤pH将标准值分为四类, 并进一步将水田(作物为水稻)和其他农用地类型(作物为小麦)分开定标, 德国和斯洛伐克为砂土、砂质壤土和黏土设定了不同的预警值, 波兰主要考虑土壤污染对地下水的影响, 根据土壤深度和水力传导率(低于和高于10-7 m ·s-1)提供了不同的值; ②建立土壤归一方程, 在土壤标准制定和标准使用过程中对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进行校准, 如中国对标准制定过程中的生物累积因子(BCF)进行归一化处理, 比利时和荷兰等在标准使用过程中, 基于土壤有机质和黏粒含量对标准进行归一化处理; ③除总量指标外, 少数国家直接采用提取态含量表征污染物在土壤中有效态浓度, 如奥地利、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这4个国家制定了土壤提取态指标, 包括硝酸氨提取和2 mol ·L-1硝酸提取, 模拟土壤-植物的污染物迁移, 表征土壤中可被作物根系吸收的重金属含量.但考虑提取剂普适性、检测方法重复性和有效态动态变化等原因, 我国暂未制订有效态标准, 待条件成熟后再行考虑.
2 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面临的问题与对策2.1 建立科学、规范的土壤环境背景值和基准制定方法
当前, 土壤环境基准在定义、概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不少争议, 但环境基准研究的目标是为制定和修订环境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与技术基础, 已被管理部门和科研单位普遍认可[25, 26].我国土壤环境背景和基准等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污灌区环境质量评价”、80年代“土壤环境容量”和“土壤环境背景值”等, GB 15618-1995标准在制定时充分借鉴上述研究成果, 转化为土壤环境基准, 以此确定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当前农用地风险管控标准是在GB 15618-1995标准基础上采用最新研究数据和方法进行了修订, 但主要还是基于“土壤环境容量”、“临界含量”和“生态环境效应”等我国土壤科学传统方法, 且不同元素的标准制定受限于数据基础, 采用的推导方法各不相同.因此, 应建立科学规范的土壤环境基准值制定方法, 为制修订土壤环境标准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
GB 15618-2018标准制定以农作物(水稻和小麦)盆栽和小区试验为主, 部分指标进行了野外土壤-农产品协同调查.盆栽和小区试验部分方法与国际生态毒理学标准方法相似, 但国内外不同研究团队的培养条件和培养时间等试验条件差异较大,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针对农作物的标准化培养试验方法; 推导方法采用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回归方法和SSD法, 但缺少对已有土壤-农作物富集数据的筛选和评估技术方法, 对回归分析和SSD方法的使用缺少指导性文件; 我国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规定的污染物类型有限, 对于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中未限定的污染物, 应建立科学地风险评估, 制定相应标准; 我国已有《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但该标准仅对地下水污染情况做监测及评价, 缺少与土壤污染情况形成关联, 随着“水土不分家”和“水土共治”等理念愈发重视, 应尝试加强保护地下水的土壤环境基准方法, 等时机成熟修订相应的农用地标准值.
土壤法实施以来, 背景值是判断土壤是否污染的重要手段.目前, 我国已制定《区域性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统计技术导则》, 有利于规范相关土壤调查和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 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壤调查和监测数据, 为确定区域土壤背景值提供依据.
2.2 加强土壤背景值和土壤环境基准等基础研究
加强土壤环境背景值和基准研究是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要求, 为制修订我国土壤环境标准提供数据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环境基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指出“国家支持对土壤环境背景值和环境基准的研究”.《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指出“制定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 应当根据环境污染状况、公众健康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环境背景值和生态环境基准研究成果等因素, 区分不同保护对象和用途功能, 科学合理确定风险管控要求”.《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制定土壤环境基准, 包括“人体健康土壤环境基准、陆生生物土壤环境基准、农产品质量土壤环境基准和地下水土壤环境基准等”.
开展土壤环境基准基础研究, 为制修订土壤环境标准提供数据基础. 4个土壤环境基准研究方向与国内外农用地土壤环境标准的保护对象一致.其中, 保护农产品质量的土壤环境基准研究, 应加强土壤-农作物可食部分污染物迁移模型及影响因子研究, 加强生物有效性在土壤环境基准制定过程中应用; 保护陆生生物的土壤环境基准研究, 应加强本土代表性土壤和典型物种的生态毒理研究, 建立生态毒理数据共享平台; 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环境基准研究, 应加强本土化暴露情景、暴露途径、暴露参数和剂量-效应评估(毒性参数)等基础研究, 服务于保护农用地使用人(口腔摄入、皮肤接触和吸入土壤颗粒等直接接触)和无食品安全限值的污染物土壤环境基准制定; 我国保护地下水土壤环境基准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 土壤环境与水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应以建立土壤污染与水环境质量标准的相互关联, 为系统化治理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夯实基础.
我国自“十五”以来,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等部门相继组织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和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等全国性调查以及土壤例行环境监测, 积累了大量土壤调查数据, 可为制定土壤背景值提供数据基础.
2.3 逐步完善土壤风险管控标准指标体系
GB 15618-2018标准基于考虑保护农产品安全、农作物生长和土壤生态, 以及具有研究数据支撑的污染物指标.其中, 基本项目(重金属)已覆盖国内外土壤标准主要重金属指标, 但我国农用地土壤标准指标数量依然相对较少.GB 15618-2018标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 不少单位提出增加锰、钴、铊、钼、钒、锑、锡、硒和氟化物等其他重金属及无机物指标.实际上, 在标准修订时最初也新增了上述相关指标的标准值, 但受到食品安全标准和支撑标准制定的研究数据限制, 上述标准主要参考国内外土壤标准值和背景值制定, 考虑风险管控标准的保护目标和筛选功能, 本轮标准修订最终未添加上述指标.因此, 下一步应在积累土壤环境基准方法学和基础数据的基础上, 考虑增加其他土壤重金属及无机物的标准值.
除指标数量, 当前我国土壤重金属指标只考虑全量指标.由于土壤的复杂性, 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在状态较多, 尤其在高背景地区, 仅以重金属总量作为污染指标往往不能起到风险筛选的作用.重金属对生物的危害是由重金属有效态所决定, 其生物有效性一直是土壤污染化学和污染生态学研究领域中的科学问题, 尤其是土壤重金属生物有效性受很多因素影响.因此, 建议在后续修订土壤标准过程中, 加强对不同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有效性关键因子的考虑(目前主要考虑pH), 尝试建立不同元素的土壤归一化经验方程, 用于基准值推导和标准值的实际使用; 针对镉和砷等对农作物质量影响较大的关键元素, 尝试建立基于提取剂的有效态指标, 补充与总量指标共同为筛选标准.
相比重金属, 我国标准中有机污染物指标较少.实际上, 标准修订过程中尝试建立石油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等指标的标准值.但考虑农用地有机污染并不是普遍存在, 且与重金属不同, 目前有机物在土壤-农作物的迁移转化规律掌握不清, 因此最终标准中有机物指标仅保留六六六、DDT和苯并[a]芘这3项.随着我国农业生产中农药和化肥的大量施用, 有机污染已成为中国土壤中不可避免的污染物质.因此, 与重金属相似, 建议后续在标准中增加有机物的种类.
2.4 鼓励建立区域或地方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
我国幅员辽阔, 土壤区域性差异极大, 各地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种植的作物类型和品种对污染物的敏感性、富集程度、水肥管理和消费习惯等都存在巨大差异.GB 15618-2018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需统筹考虑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情况.因此, 国家统一的标准一般只能起筛选作用, 在部分地区难以真实反映当地情况, 可能出现假阴性(土壤未超标但农产品超标)或假阳性(土壤超标但农产品未超标)[27]; 同时,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 土壤污染在全国尺度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 不同区域或省(区、市)的土壤污染特征并不相同.国家标准未能完全覆盖不同地区的土壤主要污染物, 因此建议组织各地环保科研团队积极进行科学研究, 制定适合于不同地域的地方标准, 作为国家标准的补充[28].
目前, 各地尚未建立地方农用地配套标准.“土十条”和土壤法中规定“各地可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这可能是地方对建立地方标准值的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同时, 农用地土壤标准制定方法、数据基础和科研团队等基础薄弱也是限制各地制定地标的原因.相比较土壤筛选值, 目前不少地方在制定或准备制定土壤环境背景值, 如已发布的深圳和韶关背景值, 正在准备制定的安徽、珠海和苏州等.考虑到背景值在当前土壤污染识别和防治的重要作用, 且制定方法相对简单, 调查数据相对充足.因此, 建立地方土壤背景值作为筛选值的补充似乎是当前一个不错的选择.
3 结论
(1) 建立科学规范的土壤环境基准和背景值的制定指南与规范, 加强土壤背景值和土壤环境基准等基础研究, 为制修订土壤风险管控标准提供理论、方法和数据基础.
(2)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逐步考虑增加土壤其他重金属及无机物和有机物标准值, 加强对土壤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考虑, 尝试建立标准使用的土壤归一方程, 建立基于提取剂的有效态指标, 作为总量指标的补充.
(3) 针对国家标准未能完全覆盖土壤区域性特征污染物, 鼓励制定适用于不同地域的地方标准, 作为国家标准的补充.同时, 在制定地方标准条件未充分的情况下, 可优先鼓励建立区域土壤背景值作为筛选值的补充.
参考文献
| [1] | Perrodin Y, Boillot C, Angerville R, et 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urban and industrial systems: a review[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1, 409(24): 5162-5176. DOI:10.1016/j.scitotenv.2011.08.053 |
| [2] | 王国庆, 邓绍坡, 冯艳红, 等. 国内外重金属土壤环境标准值比较: 镉[J]. 生态与农村环境报, 2015, 31(6): 808-821. Wang G Q, Deng S P, Feng Y H,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n soil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for heavy metal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cadmium[J]. Journal of Ecology and Rural Environment, 2015, 31(6): 808-821. |
| [3] | 陈能场, 郑煜基, 何晓峰, 等.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探析[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7, 36(9): 1689-1692. Chen N C, Zheng Y J, He X F, et al. Analysis of the report on the national general survey of soil contamination[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7, 36(9): 1689-1692. |
| [4] | 袁国军, 卢绍辉, 梅象信, 等.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延伸理解及其评价标准现状分析[J]. 中国农学通报, 2020, 36(2): 84-89. Yuan G J, Lu S H, Mei X X, et al. Extended understanding of soil pollution risk management standards for agricultural lands and the status of evaluation standards[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20, 36(2): 84-89. |
| [5] | 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S]. |
| [6] | BBodSchV. Federal soil protection and contaminated sites ordinance[Z]. 1999. |
| [7] | Swartjes F A, Rutgers M, Lijzen J P A, et al. State of the art of contaminated site management in the netherlands: policy framework and risk assessment tool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2, 427-428: 1-10. DOI:10.1016/j.scitotenv.2012.02.078 |
| [8] | Japanes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for soil pollution[EB/OL]: http://www.env.go.jp/en/water/soil/sp.html. 1991-08-23. |
| [9] | Jeffries J, Martin I. Updated technical background to the CLEA model[R]. Rio House: Environment Agency (EA), 2009. |
| [10] | 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Environment (CCME). A protocol for the deriv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health soil quality guidelines[R]. Ottawa: 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Environment, 2006. |
| [11] | ÖNORM S 2088-2. Contaminated sites Part 2: Application-specific evaluation of soil pollution of old sites and old waste dumps (in German)[S]. 2000. |
| [12] | Carlon C, D'Alessandro M. Derivation methods of soil screening values in Europe.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procedures towards harmonization[R]. Ispra: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2007. |
| [13] | Decree No. 13/1994 Sb. Decree of th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specifying some details of agricultural land resources protection[S]. 1994. |
| [14] | Official Journal of Laws No 165, item 1359. Decree of the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of 9 September 2002 on soil quality standards and earth quality standards[S]. 2002. |
| [15] | Korean Presidential Decree No. 29292, Nov. 20, 2018.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soil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ct[Z]. 2018. |
| [16] | Open Development Thailand.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guide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R]. Bangkok: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2014. |
| [17] |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Guidance manual for use of risk-based remediation goals for contaminated land management[R]. Hong Kong, China: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2007. |
| [18] | 环署土字第0970031435号令, 土壤污染监测标准[S]. |
| [19] | 环署土字第1000008485号令, 土壤污染管制标准[S]. |
| [20] | 徐猛, 颜增光, 贺萌萌, 等. 不同国家基于健康风险的土壤环境基准比较研究与启示[J]. 环境科学, 2013, 34(5): 1667-1678. Xu M, Yan Z G, He M M, et al. Human health risk-based environmental criteria for soil: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ountries and implication for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3, 34(5): 1667-1678. |
| [21] | 窦韦强, 安毅, 秦莉, 等. 农用地土壤重金属生态安全阈值确定方法的研究进展[J]. 生态毒理学报, 2019, 14(4): 54-64. Dou W Q, An Y, Qin L,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in determination methods of ecological safety thresholds for heavy metals in agricultural land[J]. 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 2019, 14(4): 54-64. |
| [22] | 李勖之, 郑丽萍, 张亚, 等. 应用物种敏感分布法建立铅的生态安全土壤环境基准研究[J]. 生态毒理学报, 2021, 16(1): 107-118. Li X Z, Zheng L P, Zhang Y, et al. Derivation of ecological safety based soil quality criteria for lead by 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J]. 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 2021, 16(1): 107-118. |
| [23] | 夏家淇.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详解[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6. |
| [24] | 王小庆, 马义兵, 黄占斌. 痕量金属元素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研究进展[J]. 土壤通报, 2013, 44(2): 505-512. Wang X Q, Ma Y B, Huang Z B. Research and prospect on soil quality benchmark for trace elements[J]. Chinese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2013, 44(2): 505-512. |
| [25] | 宋静, 骆永明, 夏家淇. 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基准与标准制定研究[J]. 环境保护科学, 2016, 42(4): 29-35. Song J, Luo Y M, Xia J Q.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criteria and standards for agricultural lands in China[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ce, 2016, 42(4): 29-35. |
| [26] | 周启星, 滕涌, 展思辉, 等. 土壤环境基准/标准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4, 33(1): 1-14. Zhou Q X, Teng Y, Zhan S H, et al. Fundament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research on soil-environmental criteria/standards[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4, 33(1): 1-14. |
| [27] | 夏家淇. 农用地块土壤污染分类标准制订方法探讨[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9, 35(3): 405-408. Xia J Q. Methods for derivation of site specific standard for management of contaminated agricultural soil[J]. Journal of Ecology and Rural Environment, 2019, 35(3): 405-408. |
| [28] | 郎笛, 王宇琴, 张芷梦, 等. 云南省农用地土壤生态环境基准与质量标准建立的思考及建议[J]. 生态毒理学报, 2021, 16(1): 74-86. Lang D, Wang Y Q, Zhang Z M, et al. The establishment of soil eco-environmental criteria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for agricultural land in Yunnan province[J]. 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 2021, 16(1): 7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