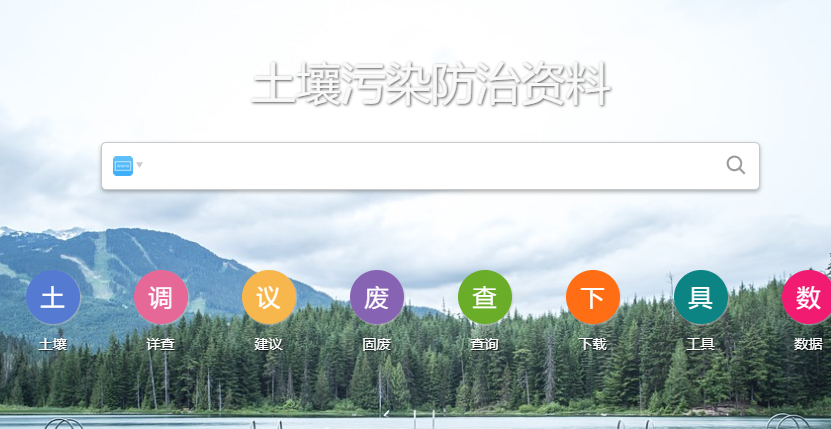环境法典编纂中“环境”“生态”与“资源”概念的关系厘定与展开
内容摘要
研究背景
我国环境立法和学理研究中存在对“环境”“生态”与“资源”的长期混乱使用,这是环境立法体系化的重要障碍。《环境保护法》中“环境”与“生态”杂糅使用,污染防治立法中“污染”的客体未按照规范性逻辑展开,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公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明。在时下环境法典研究的热潮中,学者们重点研究技术性和宏观性问题,鲜见从法律规范性、体系性角度出发解决法典编纂的规范性命题。
研究内容
本文梳理了既有立法和理论研究中对基础概念的使用逻辑,尤其是通过与《民法典》中“绿色条款”的比较,发现《民法典》中的“环境”“生态”与“资源”概念的使用不同于环境立法,“生态”“环境”在不同的规范语境中有抽象效果和具体行为客体的双重内涵,“资源”同样在不同的规范语境中存在物权客体和环境公益载体的双重内涵。环境法典的编纂中需要厘定基础概念的规范性意义。首先,应区分规范性概念和事实性概念,“环境”侧重于描述事实,属于实证法视角下的抽象概念,其主要功能为联结法律调整的生活事实,而“生态”则表述“环境”的某种功能或特征,二者不可作为并列的法律调整对象,否则会产生过于宽泛的解释空间,且难以把握“环境”范围。其次,应当对抽象概念进行具体化。作为抽象概念的“环境”流入规范时,须借助其他相关概念进行具体化,以把握其规范性特征,现有环境立法中“环境”在抽象和具体层面交替使用,并未以规范性思维对其进行具体化。最后,基础概念应当体现环境利益精确化区分与利益衡量,整合“污染”的客体与环境公益的范围。
研究结论
在环境法典编纂中,宜将“环境”作为抽象概念,作为联结内部规范与外部事实的工具,避免概念含糊,将“生态环境”“环境资源”作为抽象概念,更不应将“生态”与“环境”并列为两种不同的调整客体。“环境”的规范性意涵或事实性范畴的具体化应当交由“生态”与“资源”进行辅助说明,强调“环境”在规范视角下的某种特征。《民法典》与环境立法的衔接问题可交由法解释学。同时,环境法典调整的范围应当由抽象客体转向具体行为,全面系统展开对行为本身的定性、后果等规范性问题的考量。基础概念的展开也应当注重对利益的识别与调节。环境法典编纂若不解决诸如基础概念等规范性问题,法典化将成为伪命题,仅具有形式而不具备实质。